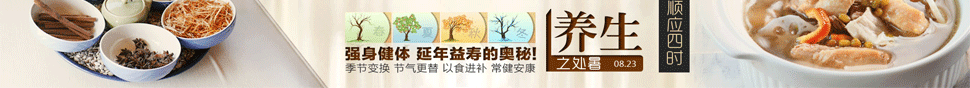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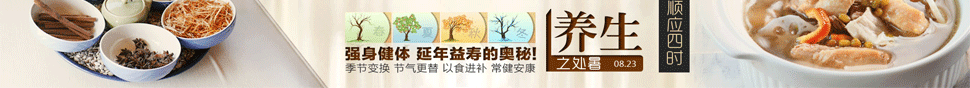
麻黄附子甘草汤就是甘草麻黄汤加附子而构成的,也就是《金匮要略》的麻黄附子汤。甘草麻黄汤与麻黄附子汤都是治疗水气病的药方。《金匮要略》水气病篇云:“里水……甘草麻黄汤亦主之。”“水之为病,其脉沉小,属少阴。浮者,为风;无水虚胀者为气。水,发其汗即已。脉沉者,宜麻黄附子汤;浮者,宜杏子汤。”根据《类聚方广义》的记载,甘草麻黄汤证主要是呼吸困难,喘气,或者自汗,或者无汗;而麻黄附子汤证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更加恶寒或者身上微痛。
《金匮》麻黄附子汤的组成是:麻黄三两,甘草二两,附子一枚(炮)。而宋本少阴病篇的麻黄附子甘草汤的组成是:麻黄二两,甘草二两,附子一枚(炮)。麻黄的用量在麻黄附子汤比麻黄附子甘草汤多一两,其方名也有所变动,但是药方中药物排列的次序依然保持康治本方中药物排列次序的规矩,都是由麻黄甘草基加附子。
甘草麻黄汤最早出现在《金匮》水气病篇:“里水……甘草麻黄汤亦主之。”条文中甘草麻黄汤是治疗“里水”的,其实这里的“里水”应该是“皮水”之误,也就是说甘草麻黄汤是治疗阳性水肿的药方。
我们现在分析一下甘草麻黄汤的组成,它是由甘草二两、麻黄四两所组成的,治疗喘息急迫、呼吸非常困难、或自汗或无汗。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方是属于和法的方,也就是利尿的方。甘草麻黄汤通过利尿,把造成呼吸困难的胸腔部、肺部的水排掉,甘草麻黄汤证可以自汗,也可以无汗,就是说有汗或无汗都可以用甘草麻黄汤,可见它不是发汗的作用。初学者有一种思维惯性,一看到麻黄就觉得会发汗,我初学时也不例外。其实,这个思维惯性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麻黄只有跟桂枝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发汗,而跟石膏、跟甘草在一起就不一定发汗,所以甘草麻黄汤自汗、无汗都可以治!
《金匮要略》的麻黄附子汤后来转到宋本《伤寒论》里作为少阴病第条条文的时候,明显是作为一种治疗表阴证的方子,考虑到少阴病的阳虚,不同于治疗水气病,因此麻黄就由三两减为二两。麻黄附子甘草汤证的特异性症状是没有发热的,前面我就这个问题曾经给大家讲过,但是在表阴证的反发热时也可以使用。后来发现表阴证的患者带有水饮,腹证出现心下有悸动时,就在麻黄附子甘草汤证的基础上,加了细辛二钱,而去掉储水的甘草。细辛这味药能够祛痰饮,能够治疗心下的悸动。
不要认为麻黄附子甘草汤一开始就出现在宋本里面,就是规定治疗恶寒发热、脉象沉弱的病证,其实它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是从治疗水证、治疗哮喘以后,才慢慢地转化而来的。作为宋本里面的第条条文应该是借用了这个方子,因为使用有效所以后来就把它记在治疗外感发热的病证中了。
我想通过一个病例,再把它们的临床应用讲一下。
这是40年前,我刚用经方看病的那几年所碰到的一个特别重的病例,这个病例的治愈对我自已建立学习经方的信心的确有非常大的作用。
年的农历四月,我从状元村赶到了永强我二妹家里,3岁的外甥阿津病了,麻疹后持续发热半个月不退。二妹夫的叔叔是当地有名的西医儿科医师,半个月来一直给孩子注射青霉素等抗生素。注射后热度依然持续不退,但他认为白细胞高必须继续使用青霉素。
二妹夫的父亲略知医道,发热后给孩子煎服羚羊角片十多次,然而症状更趋恶化。我的二妹夫出差在外省,一时半会儿联系不上,我赶到二妹家中时,她全家人正急得团团转,医院住院治疗。二妹求我赶紧给小外甥诊治。刻诊:病儿肢体消瘦,精神萎靡,表情淡漠,面色淡白,安静嗜睡,鼻流清涕,喜衣被,不渴厌食,小便清长,手足凉,额有冷汗,舌质淡,苔薄白,脉沉细无力,脉搏次/分,白细胞为19.0×/L、中性粒细胞72%,血红蛋白9g/L,体温37.4℃,腹肌菲薄而稍紧。针对以上症状,我认为这正是少阴病的“脉微细,但欲寐”“反发热”的麻黄附子细辛汤证。我二妹夫的父亲认为发热就是热证,大暑天使用麻黄附子细辛汤这样的热性药极其危险。我却坚信此方必定有效,所以力排群议投一剂麻黄附子细辛汤(生麻黄2g,附片6g,细辛2g)并停用一切西药。
家里人去寺前街中药店抓药的时候,店里老药工听说这一帖麻黄附子细辛汤是给发热的小儿服的,十分害怕,千叮咛万嘱咐之后オ给抓了药。抓好了药,算盘一算,药价一共只有七分钱。老药工摇摇头说:“我一辈子没有抓过这么凶险又那么便宜的方子。”
服药后5小时,外甥精神大有起色,体温即恢复正常,手足亦稍温,日内排出臭软便二次,鼻水、冷汗均消失。这正如陆渊雷先生所说的:“少阴病,在治疗中,手足温、下利为正气恢复,抗病所生之代谢废物积于肠间者因以排除显为阴证回阳之机。”我知道表证已解,正气将复,连投三剂附子汤,第四天复诊时外甥已能自行下床嬉戏,大便、体温均转正常,唯稍怕冷,易疲劳,脸色仍白,脉细沉,舌尘较前稍红,血检为白细胞16.6×/L、中性粒细胞76%。继予附子汤7剂,药后则证情日趋进步,渐致复常。此证在我诊后的第11天血检才达正常,白细胞为9.8×/L,中性粒细胞42%,嗜酸性白细胞也出现了。西医认为嗜酸性白细胞的出现,可能是警报解除的一个标志。这个病就这样治好了。
这病治好以后,就是说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治好了如此严重的、体能虚弱的感染型疾病,这件事在当时那个地方就像是一个新闻一样,也的确给我自己带来了动力。我后来在想,当时投这个方子虽然治好了,但有没有问题呢?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呢?这个小孩没有心下悸动,同时他的体能是虚的,假如投麻黄附子甘草汤可能会更好一点。为此我专门写了一个总结,说明病虽治好了,但并不是完全对证。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不对证,为什么会治好呢?我觉得整个方向是对的,只是差了一点点,所以有的病虽然治好了,但我们自己也应该总结一下。就像打靶一样,靶是打上了,但不是十环,没有丝丝入扣,在药证方面还差一点。这以后我在临床上也经常运用这个方子,用了很多,特别对一些年老的、体弱的、妇女产后的,假如是外感初期,出现体能差、恶寒、乏力脸色苍白、脉象沉弱无力的,基本上用这个方子就非常得当。老人体能差的,突然耳朵聋了,突然出现鼻孔塞住或者一下子出现了我们还估计不到是怎样的一种病证时,都要考虑这个“始得之”,在发病的短期内用此方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假如时间拖久呢,就不一定了。
针对麻黄附子细辛汤证我还要总结几句话。
一是,它不一定发热。在使用过程中,只要掌握住病始得之,脉象沉微,恶寒,又特别疲劳,就可以用这个方子。有外感的话可有发热,没有外感就不一定发热。有时候患者体温很高,但是他自已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发热,这还应该算是恶寒的。要注意的是,麻黄附子细辛汤,应该是由麻黄附子甘草汤派生出来的,它应该是在麻黄附子甘草汤证基础上,有一个心下悸动、痰饮的症状,因此临床应用非常广泛。体能差的老人感冒,不管发不发热都用这个方子;还有支气管炎、支气管炎哮喘,出现精神特别差的,或者脉象特别弱、沉的,也要考虑这个方子;还有一些老人、产妇,体能差,精神差,出现了带状疱疹,马上用这个方子,可能这个疱疹就不会迁延下去。现在带状疱疹西医有比较好的办法,但是后遗症也避免不掉,弄不好会拖延5~10年,所以最好一开始就用中药、针灸治疗。
二是,这个方子对清鼻涕多,甚至鼻闭,只要符合体能差、脉象沉弱,都可以用;中耳炎、耳鸣也可以用;暴聋、暴哑,只要出现特异性症状,体质非常弱,恶寒明显,脉象沉弱,身上有疼痛,就可以用;还可以治疗咽喉疼痛,咽喉疼痛并不是我们常讲的实热,表阴证很多时候也会出现咽喉疼痛,仔细看的话咽喉里面肿而不红。彭坚老师就曾用麻黄附子细辛汤成功治疗过一个声音沙哑的患者,这个患者是位省领导,第2天就要做报告,当时心情非常着急就找彭老师,患者几乎不能发声,看其咽喉也不红肿,有很多白色的分泌物。彭老师就开了一帖麻黄附子细辛汤,喝下去以后,患者的声音就明显好转,第2天做报告一点障碍都没有。可见这个方子很厉害,用得好,对一些急性病、严重的病,都可以有很好的效果。
三是,在宋本《伤寒论》少阴篇里面提到,麻黄附子细辛汤的病证也可以用针灸,特别是灸。宋本第条提道:“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就是说当少阴病下利,出现呕吐,大便次数多,可以用灸的方法。第条提出:“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这个条文在承淡安的《伤寒论新注:附针灸疗法》里到这里就结束了,但实际上在宋本里“当灸之”之后还有“附子汤主之”,即灸和用药同时进行,这都是在强调灸对治疗是有用的。那出现这个病证应该灸哪里呢?条文里没有交代,历代很多人认为是灸膈俞等,承淡安则主张灸大椎七壮,认为假如这个病证符合于少阴病刚起的症状,没有出现四肢冰冷四逆汤证的话,灸大椎就可以;假如出现四肢冰冷的四逆汤证,还要灸关元。可见针灸和方证内外合治应该是最好的!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原书条文比较简单,仅仅依据条文的叙述对这两个方子特异性症状的把握,在初学时还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想应该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从不同的角度来掌握如何去鉴别。大塚敬节有个病例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鉴别方法。
一个患者哮喘,这是他从小就有的痼疾。大塚敬节看了以后,觉得这个患者恶寒,鼻涕像清水一样,咳嗽气喘,痰液也似清水样,符合小青龙汤证,就给他开了小青龙汤,但是没有疗效,吃了几次都没有效,就不给他吃了。这个患者为了把病治好,就自己看书琢磨,他觉得自己体能已经差了,虽然外表看不出来,脉象也不一定看出来,但从病史分析、从自己的年龄分析应该是,于是他就给自开药方,开的就是麻黄附子细辛汤。结果疗效特别好。大塚敬节得知后,就把这个病例公布了出来。医生有时候治不好,患者反而自己治好了,这个一点不奇怪。大塚敬节感到很高兴,说麻黄附子细辛汤他当然非常熟,可为什么没有开给他呢?就是因为被表面的症状遮住了,也就是说这个病证在他身上可能还是一种隐证,只有他自己了解自己的体能,外面的脉象、精神状态看不出来,而作为医生总是以外面的脉象、精神状态作为指标,所以就认为没有虚,其实这个是内虚,潜在的虚,患者自己把它抓出来了,所以就治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方证辨证,虽然语言上讲都是对的,但是实际还是不够的,有时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情况。就像前面讲的曹颖甫夫人潘氏的病案,没注意体质弱,以为脉象浮紧有力,就是麻黄汤证的脉象,其实此患者是脉证不符。大塚敬节也一样,这个患者他开了小青龙汤,脉证应该是相符的,但是为什么没有效?因为这个病的潜证是麻黄附子细辛汤证,当时没有看出来,是患者自己慢慢研究出来的,这个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临证时不要全部以外表的症状作为一个终点,这只是一个起点,可以作为一个条件,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进一步探究。
鉴别非常重要。要鉴别哪些情况呢?刚才讲的小青龙汤当然要鉴别,虽然大塚敬节也没鉴别出来,但还是要把它鉴别出来。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比他高明,而是说明病证的潜在性、复杂性。大塚敬节看不清楚,患者自己慢慢研究出来治好了,说明他是方证相对应的,也说明方证相对应不是那么容易的。
小青龙汤证是咳嗽气喘有痰,痰液清稀,鼻涕也是清水一样,腹部的弹性中度,心下痞硬,胃中停水。大塚敬节开始诊察的时候,肯定是符合的。但是这里没有体质状态,体质状态只有患者自己オ会感到,所以问诊还要全面、仔细。这就是小青龙汤证和麻黄附子细辛汤证的区别,对照一下就知道了。麻黄附子细辛汤证这些症状几乎都有,但是精神感到非常萎靡,元气不足;或者病史很久了,体能搞差了,这都应该考虑;或者病刚起,但看上去精神很差,好像矛盾,其实这些都是它的范围。这就是我前面所讲的默会知识,有时候用语言难以完全表达清楚,要慢慢地从多个方面去体会。
还有跟四逆汤证鉴别。四逆汤证形寒肢冷程度非常严重,手脚冰冷的,而麻黄附子细辛汤证就不一定。四逆汤证还有下利清谷、冷汗不止、脉象沉细的程度更明显,腹证更软,这都是跟麻黄附子细辛汤证不同的地方。
吴茱萸汤证也属于阴证,也有头痛,甚至头痛严重,但同时有手脚冷、干呕上冲,特别是干呕上冲这个症状一般是麻黄附子细辛汤证所没有的。
还要跟附子汤证进行鉴别。恶寒、脉沉、身体疼痛,麻黄附子细辛汤证都有,但是骨节疼痛、背部特别冷这两个症状一般是没有的。
芍药甘草附子汤证也有恶寒,但是没有表证,一般不会出现表证的状态。
最后再强调一下麻黄附子细辛汤证的状态,人体能非常差,表现为贫血貌,全身都感到疲倦,有恶寒,有咳嗽气喘、痰液清稀,鼻涕也是清的,所以容易跟小青龙汤证混淆;小便是清的,甚至多尿,但有时候也有小便不利;身体比较重,腹部柔软无力,这就是它所表现的一个全方位的状态,临床并不是全部都会显现出来,但是要把它理解了,慢慢地就会进入状态。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