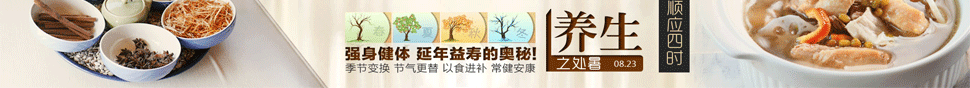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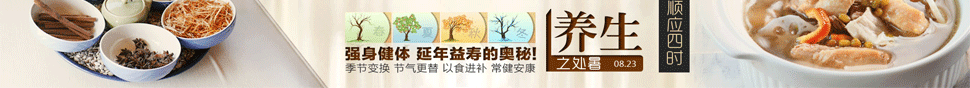
随着祖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东北人也把我们当地各种特色美食带到了祖国的各个角落。一说起东北菜,大家就会不自觉的想到“锅包肉”“杀猪菜”“溜肉段”“烧茄子”,这些大家早都耳熟能详了。
锅包肉今天我就来说说你们不但没有吃过都不一定见到过的,我儿时却常吃的东北特色“美食”
首先就是专属于我们东北的“灶坑烧烤”
听到这个美食种类是不是大家都一头雾水?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东北的火炕,火炕都会有一个添柴烧火的小门,我们都叫作“灶坑”,还有烧火做饭的“大锅灶”都有这个“灶坑”。
儿时的大灶台所谓的“灶坑烧烤”就是当柴火燃烧透之后,会变成温度很高的类似于炭火的状态,这时我们把一些土豆,地瓜,玉米,鸡鸭鹅蛋,还有一些“小野味儿”放入其中烤制。烤熟之后那不但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真是别有一番风味,现在回味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
其中我最爱吃的还是烧制那些“小野味儿”。所谓“小野味儿”就是我们儿时用“弹弓”打到的一些“家雀”,最常吃的还是“麻雀”。打到的“麻雀”不需要拔毛整只的放进去烧烤,待“灶坑”里的炭火几乎快燃尽的时候,把外表“烧焦的麻雀”扒拉出来,然后拔去外面烧焦的部分,里面的肉真的是特别的香甜,连骨头都会嚼了。
我们儿时的弹弓几乎都是我们自己制作的,首先会去树林里寻找“Y”形状的树枝,然后用刀修理好,再用废弃的自行车内胎剪成“皮条”。用妈妈“纳鞋底”的线绳绑在“Y”型树枝的上面两头,放“子弹”的后堵,我们也是用废弃的皮子剪出来的。
儿时的弹弓所谓的子弹就是一种用黏土做成的“小泥球”,儿时我们都是去到河边“抠”来那种黏性很高的黄泥,再团成一个个小圆球形状,晒干之后就变成了我们的“子弹”。
第二个让我至今回味的就是“大酱炖蛤蟆”。
我们叫作“蛤蟆”。儿时一开春,当大地开始“化冻”之后,就是我们“动手”的好时机了。三五个小伙伴,拎着一个大袋子就朝着大河边出发啦。
我们都管这种行为叫作“抠蛤蟆”。这也是需要“经验”的,为什么是大河边?因为蛤蟆快入冬的时候,就会找地方冬眠。夏季时都在大河里,所以都是就近挖洞进行冬眠的。
而开春的时候,它们就会从深土层爬到浅土层来,但不会爬出来,这就需要经验才可以才可以找到它们了。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具体怎么判断哪里的土下面会有青蛙已经记不得了。大概是看着表面的泥土是否有松动的痕迹?有知道的朋友么?
(怕有些朋友看到引起不适就不配图了)
那时我们都会收获满满,有时是平均分配了,有时是谁抠的就是谁的,当然也有“分赃不均”的时候会干上一架。也有和谐的时候,统一拿去一个人的家里,让他的父母给用大酱炖上,大酱炖蛤蟆是真的香啊!
第三个就是“黑黝黝”
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知道这种美味的,一种类似“姑娘”的秧苗的植物。上面会结出一颗颗紫黑色的小小的圆球,吃起来甘甜还带着一股特别的味道。真的很好吃,也有结出绿色小圆球的,我们叫它“绿幽幽”。
听说学名叫龙葵儿时一到快入秋的时候,田地间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黑黝黝”。我们会拿上罐头瓶子,边寻找变采摘,每次都是一个罐头瓶子装不下,裤兜都会揣上一些。
现在很少能看得到这种植物了。
还有很多很多的儿时难以忘怀的美味,比如高粱地里结出的“wumen”。还有类似高粱又类似甘蔗的一种植物,我们那时叫“甜杆儿”。还有一簇簇的红彤彤的“酸丁子”。还有水沟边长的一种细长的绿绿的叶子,吃起来酸酸涩涩的,但是会回甘。还有一种长在大河里的一种植物,会结出三棱角黑色外壳的果实,果实剥去外壳是白色的果肉,吃起来“面面”的口感,微微的发甜,我们叫它“羚羊角”。还有一种叫作“老苍子”的东西,外壳全是刺,里面的果肉是酸甜的。
刺梨写了这么多,突然发现也许我们怀念不仅仅是儿时这些“野味”的味道,还有那些纯真美好的回忆,更有那挥之不去的思乡之情。

